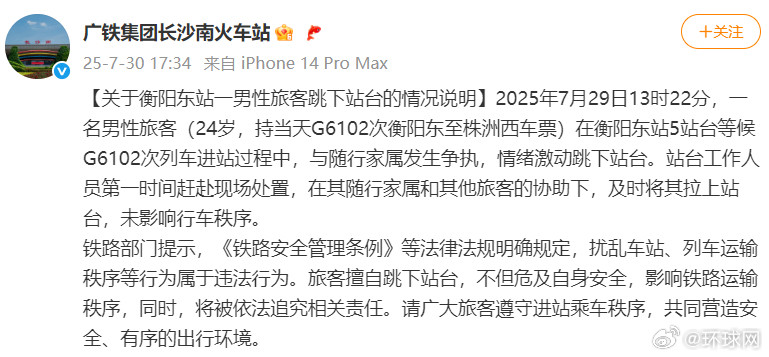江苏南京,女友去世后,男子自愿赡养女方父母,双方共同生活了20多年。可女方父亲临终前,突然留下公证遗嘱:把自己的房产份额全部留给自己的大女儿。男子傻眼了:我们之间明明签了赠与协议,你们两老口把2楼的3间房给我了的。双方对簿公堂,可法院的判决结果却让男子意外。南京老宅的二十年冷暖朱小伟蹲在拆迁办门口的石阶上,手里捏着那张泛黄的《房产分割协议》,纸角被汗水浸得发皱。二十米外,戴阿姨正被大女儿扶着往巷口走,背影佝偻得像株被霜打过的向日葵。二十三年前的那个雨夜,他还叫韩文。19岁的他骑着借来的摩托车,载着女友朱梅在城郊公路上飞驰,迎面撞上了一辆失控的货车。朱梅没能撑到医院,他左臂缝了十七针。在殡仪馆,朱梅的父亲老朱,一个开修配厂的糙汉子,红着眼圈却没打他:“事已至此,你走吧。”可韩文“咚”地跪在水泥地上,额头磕出青包:“叔,梅梅没了,我给你们当儿子,养老送终。”戴阿姨搂着他的头哭了半宿,第二天一早,把户口本拍在他面前:“改个名吧,随我们姓朱,叫小伟。”朱小伟搬进了老朱家那栋两层小楼。一楼堂屋摆着朱梅的黑白照片,他每天早上都要擦一遍相框。老朱的修配厂缺个帮手,他跟着学拧螺丝、补轮胎,手上磨出的茧子比老朱的还厚。戴阿姨有风湿,每逢阴雨天,他就烧好艾草水给她泡脚,膝盖上的淤青是给她按揉时硌的。2005年朱小伟结婚,新娘是戴阿姨托人介绍的。婚礼上,老朱喝多了,拉着亲家的手说:“小伟就是我亲儿子,这楼上三间房,将来都是他的。”2017年夏天,戴阿姨把朱小伟叫到堂屋,老朱已经在桌上铺好了纸。“小伟,立个字据吧,免得以后你姐有想法。”老朱递过钢笔,协议上写着:“二楼三间归朱小伟一家三口,一楼归老两口。”朱小伟签字时,笔尖在纸上洇出个小墨点,像颗落在心尖的痣。变故是从2019年秋开始的。老朱咳得直不起腰,查出胰腺癌时,癌细胞已经转移了。住院第一天,医生拿着五万块的进口药单子,朱小伟攥着缴费单在走廊里打转。“爸,要不咱用国产药?效果差不多,能省三万。”他进病房时,声音比蚊子还小。老朱正在输氧,闻言扯掉管子:“我养你二十年,现在我要救命,你跟我算这个?”那天下午,戴阿姨悄悄塞给朱小伟一个存折:“这里有两万,先拿着。你爸就是气头上,他知道你难。”可裂痕已经有了,朱小伟去医院的次数渐渐少了,有时戴阿姨打电话,他总说厂里忙。2020年清明前,老朱突然精神好了,让戴阿姨叫来了大女儿。他撑着坐起来,在公证处的人面前,声音微弱却清楚:“我名下房产份额,全给大女儿。”朱小伟是在老朱头七那天知道遗嘱的。朱大姐把公证书拍在他面前,香烛的烟飘在两人中间。“小伟,不是姐狠心,爸说了,这房子不能给忘恩负义的人。”“忘恩负义?”朱小伟抓起供桌上的苹果就摔,“我在这伺候二十多年,给你爸端屎端尿,你说我忘恩负义?那协议呢?白纸黑字!”“协议没过户,不作数!”朱大姐提高了嗓门,“我爸住院最后俩月,你去过几趟?”法庭上,戴阿姨坐在原告席,眼神躲闪着被告席上的朱小伟。“法官,我现在也不同意给小伟房子了。他后来对我们确实不好……”朱小伟的律师翻着二十年来的缴费单:“煤气费、电费、医药费,这些都是我当事人缴的。他只是没满足老人所有要求,不代表没尽赡养义务。”法官敲法槌时,窗外的梧桐叶正往下掉。“房产赠与以登记为准,公证遗嘱撤销赠与合法有效。朱小伟一家,三十日内搬离。”搬家那天,朱小伟的儿子抱着玩具车问:“爸,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奶奶家?”朱小伟没说话,只是把那张泛黄的协议塞进了纸箱底层。戴阿姨站在门口,看着他们把东西搬上卡车。当朱小伟发动汽车时,她突然追出来,塞给他一个布包。“里面是你这些年给我们的钱,我攒着呢。”卡车开出巷口时,朱小伟从后视镜里看,戴阿姨还站在那,像株被风吹歪的向日葵。他突然想起刚改名那天,老朱教他认修配厂的零件,阳光落在两人手上,都带着机油的光。有些账,法律算得清;有些情,却像没过户的房子,住再久,也可能一夜清空。


![这几天方丈大师被各路精英玩坏了[大笑]你还别说方丈大师这肥头大耳光头样貌,](http://image.uczzd.cn/3801357417470192410.jpg?id=0)